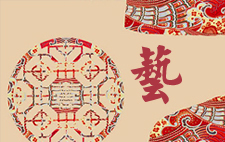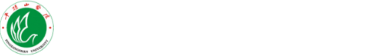限定内容
主题
- 101,077 篇 诗歌
- 33,853 篇 文学作品
- 25,869 篇 现代文学
- 23,203 篇 诗集
- 12,662 篇 文学
- 11,731 篇 中国
- 6,810 篇 当代文学
- 5,826 篇 诗人
- 4,809 篇 当代作品
- 4,730 篇 诗歌创作
- 3,751 篇 诗歌教学
- 3,248 篇 意象
- 3,020 篇 新诗
- 2,107 篇 古典诗歌
- 2,082 篇 当代
- 2,044 篇 诗歌鉴赏
- 1,350 篇 课外阅读
- 1,323 篇 民歌
- 1,313 篇 高中语文
- 1,198 篇 杜甫
机构
- 936 篇 西南大学
- 934 篇 华中师范大学
- 755 篇 南京师范大学
- 732 篇 首都师范大学
- 695 篇 四川大学
- 688 篇 北京师范大学
- 642 篇 福建师范大学
- 601 篇 陕西师范大学
- 560 篇 山东大学
- 544 篇 北京大学
- 524 篇 西北师范大学
- 512 篇 南京大学
- 503 篇 河北师范大学
- 496 篇 武汉大学
- 474 篇 上海师范大学
- 459 篇 复旦大学
- 441 篇 河北大学
- 440 篇 苏州大学
- 429 篇 安徽师范大学
- 417 篇 广西师范大学
相关文献
- 从修辞学角度看诗歌《不要温顺地走入那个 良宵》与电影《星际穿越》的共鸣效果
-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维普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基于学习任务群的诗歌写作教学探究
- 深圳市宝安中学(集团)外国语学校 广东深圳518101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维普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“意境”作为文学思想成型的简要梳理——从魏晋至唐的诗歌和文论出发
- 南开大学 天津300071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博看期刊(平顶山学院)
 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论王计兵诗歌中的自我体认
-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维普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论张枣诗歌中的对话性
-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博看期刊(平顶山学院)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博看期刊(平顶山学院)
详细信息
 欢迎光临图书馆智慧平台!
欢迎光临图书馆智慧平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