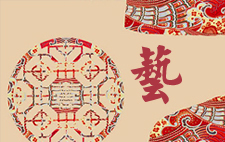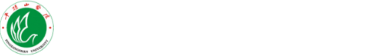限定内容
主题
- 101,077 篇 诗歌
- 33,853 篇 文学作品
- 25,869 篇 现代文学
- 23,203 篇 诗集
- 12,662 篇 文学
- 11,731 篇 中国
- 6,810 篇 当代文学
- 5,826 篇 诗人
- 4,809 篇 当代作品
- 4,730 篇 诗歌创作
- 3,751 篇 诗歌教学
- 3,248 篇 意象
- 3,020 篇 新诗
- 2,107 篇 古典诗歌
- 2,082 篇 当代
- 2,044 篇 诗歌鉴赏
- 1,350 篇 课外阅读
- 1,323 篇 民歌
- 1,313 篇 高中语文
- 1,198 篇 杜甫
机构
- 936 篇 西南大学
- 934 篇 华中师范大学
- 755 篇 南京师范大学
- 732 篇 首都师范大学
- 695 篇 四川大学
- 688 篇 北京师范大学
- 642 篇 福建师范大学
- 601 篇 陕西师范大学
- 560 篇 山东大学
- 544 篇 北京大学
- 524 篇 西北师范大学
- 512 篇 南京大学
- 503 篇 河北师范大学
- 496 篇 武汉大学
- 474 篇 上海师范大学
- 459 篇 复旦大学
- 441 篇 河北大学
- 440 篇 苏州大学
- 429 篇 安徽师范大学
- 417 篇 广西师范大学
相关文献
- 论梅尧臣对西昆体的继承与创新
- 甘肃长河科技专修学院 甘肃兰州730030延边大学文学院 吉林延吉133002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浅析王书怀乡土诗歌的美学特征
-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157000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博看期刊(平顶山学院)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博看期刊(平顶山学院)
详细信息
- 语言建构:审美鉴赏的有效路径——以《迷娘(之一)》《树和天空》为例
- 酒泉市肃州中学 甘肃酒泉735000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多元化译者身份与翻译的跨场域建构——以赤松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为例
- 长安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撒拉族民族文化心理的当代诗歌呈示——以马丁的诗集《家园的颂辞与挽歌》为例
- 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历史迭转中“同治中兴”诗歌的众声与别调
-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215123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博看期刊(平顶山学院)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博看期刊(平顶山学院)
详细信息
- 课程视域:综合性学习单元作业设计策略——以“轻叩诗歌大门”教学为例
- 江苏苏州市金阁实验小学校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维普期刊数据库
 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同方期刊数据库
详细信息
- 原型–模型翻译论视角下中国诗歌英译的可行性——以《长恨歌》译本比较分析为例
-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
-
来源
 维普期刊数据库
汉斯期刊
维普期刊数据库
汉斯期刊
详细信息
 欢迎光临图书馆智慧平台!
欢迎光临图书馆智慧平台!